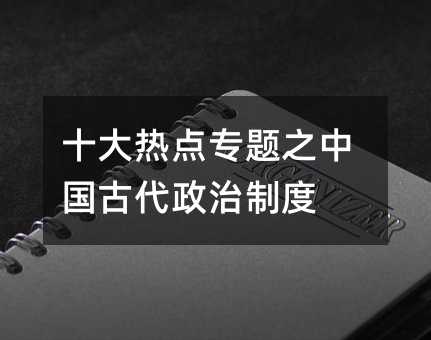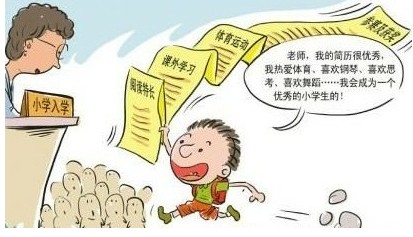《装在套子里的人》写于1898年,是契诃夫出色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在契诃夫的简短小说中算是比较长的,但也不过一万字多一点。其故事也不复杂。主人公是一位在中学里教希腊语的中年教师,名叫别里科夫。现实生活让他一直感到心神不安,让他害怕,为了同世人隔绝,不致遭到外面的影响,他总想给自己包上一层外壳,给自己制造一个所谓安全的套子:就算在艳阳天外出他也一直穿着套鞋,携带雨伞,他的雨伞、怀表、削铅笔的小折刀等等所有能包裹起来的东西都一直装在套子里,就连他的脸也仿佛装在套子里,由于他一直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面,戴着黑眼镜,耳朵里塞上棉花,坐出租马车的时候也要车夫立刻把车篷支起来。这只是他抵挡恐惧的外在表现。其次,所有被禁止的东西都让他感到心里踏实、了解明了,而对所有没被政府明令禁止的事物他都感觉可疑、害怕。他的一句时时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千万不要闹出什么乱子来。”在这部篇幅不算长的小说里这句话居然以不一样的方法出现了九次之多,简直就像咒语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特不要让人没办法容忍的是,他一直像一个幽灵一样不请自到地造访每一个教师的住所,一句话不说地坐上一两个钟头,然后又像幽灵一样地消失了。他的恐惧像毒瘤一样一点一点地蔓延,传染给他周围的每个人。他在学校里待了15年,整个学校乃至全城被他如此的情绪控制了15年,居然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没一个人想要反抗,想要对他说一个不字。同学们可以想像一下,那是什么样的15年啊!全城的人什么都怕: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寄信、交朋友、念书,不敢周济没钱人、教人识字,不敢吃荤、打麻将,不敢搞任何娱乐活动,大家都像他一样蜷缩在我们的套子里苟且偷生。
而最可怕的是,日渐地,这所有都成为了习惯,成为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大家可以明显地领会到这一点。别里科夫去世了,死得很具备戏剧性:学校里新来了一位史地教师,从乌克兰来的,与他一块儿的还有他的姐姐华连卡,他们的到来好似一块石子一样把死水一潭的沉闷生活搅起了涟漪。乌克兰是俄国的南方,那里气候宜人,一直阳光灿烂,那里的人的性格特点也受了那种地理环境的影响,豪爽,快乐,活泼,这一点很鲜明地体目前华连卡身上。小说中是如此形容她的:她简直就像蜜饯水果,活泼极了,非常爱热闹,总是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扬声大笑;她就像一个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美神一样从浪花里钻出来了;小俄罗斯女性只能哭或者笑,对她们来讲不哭不笑的心情是没的……如此的快乐甚至也感染了“套中人”别里科夫,在众人的怂恿下他甚至计划向华连卡求婚了,不过也只是计划罢了:婚后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把他给吓住了,特别让他害怕的是华连卡姐弟两人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法,他觉得他们为人师表居然骑着自行车穿街而过简直不成体统,以华连卡如此的活泼性情,可能将来就会惹出什么麻烦来。于是他来到华连卡弟弟那里,告诉他这不应该那不应该,这不对那不对,最后被这个火暴脾气的弟弟揪着脖领子从楼梯上推了下去,而这恰巧被华连卡看到了。别里科夫又怕又羞,过了一个月就一命呜呼了。别里科夫就如此极具戏剧性地死去了。学校与城里的人以为就此可以享受解脱的自由了,而悲哀的是,这种恐惧的情绪已经渗透到每个人的血液中去了,好心情持续了还不到一个星期,生活又恢复了老样子,照先前一样,仍旧那样压抑、沉闷。
如此的生活什么时间才是头呢?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在小说的结尾处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剖析得非常有道理,他觉得:“自己遭到委屈和侮辱而隐忍不发,不敢公开声明站在正直自由的人一边,反而自己也弄虚作假,面带微笑,而如此做无非是为了混一口饭吃,为了有一个温暖的小窝,为了做个不值钱的小官罢了。”这就是根源所在,为了保全自己、为了一己私利而丧失人格,丧失做人的尊严,丧失做人的起码原则,如虫豸一般苟延残喘。
如此的例子在契诃夫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变色龙》中的警察奥楚蔑洛夫因狗的主人的不同而瞬息万变的态度活脱脱地勾画出一个丧失人格尊严的势利小人的丑恶嘴脸;《一个官员之死》中的小官吏仅仅由于在戏院看戏时打了个喷嚏,唾液喷到前面一个大人物——将军的头上,而因此变得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尽管将军并不在乎,他却一次次地找上门去讲解,到最后倒真的把将军弄烦了,对他疾言厉色起来,而他最后也居然由于如此一个极偶然的事件丧失了性命,那情景简直叫人不忍卒读。契诃夫以细腻的手法描写了主人公的心理变化,揭示了精神上的奴性是多么害人,多么可怕,对人心灵的毒害是多么巨大,一个丧失了人格尊严的人是多么地猥琐……
这类都堪称契诃夫创作中的经典。契诃夫有很多的中简短小说和戏剧作品都在表现同一个主题:奴性和奴性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心理。契诃夫或许是俄罗斯第一位作家,认识到资金、官职、权威和权力不过是奴役的外部缘由,而奴役真的的工具是恐惧。恐惧使得《装在套子里的人》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恐惧使得他的同事们敢怒不敢言。而恐惧产生的根源是渗透在人骨子里的奴性和漠然。试想想,假如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每个人都能把自己当成顶天立地的人,能互有关心,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打破,而不是在别人身上寻高兴。那样,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内心如何可能被恐惧牢牢地控制住呢?人还有哪些必要把自己装在“套子”里呢?
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结合契诃夫1892年完成的小说《恐惧》来理解。这部名为《恐惧》的小说,可以说,是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的绝好解释,通过它大家可以更深刻、更准确地理解《装在套子里的人》所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对什么都怕,而缘由呢?照他一个人的话说:“我领会到生活情况和教育把我限制在狭小、虚伪的圈子里,我的全部生活无非是易教网花尽心思欺骗自己和其他人,而且自己并不感觉。……我想像到我一直到死都摆脱不了这种虚伪,就心里害怕。……大家总是不公道,对人造谣中伤,破坏彼此的生活,把大家的全部力量都浪费在大家无需的而且妨碍大家生活的无聊事情上。……我怕大家,是由于我不知道他们。……我不知道人为了什么原故要生活下去。”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契诃夫在日记中写过如此的话:“世界上没一个地方像大家俄罗斯如此,大家遭到权威的这样压制,俄罗斯人遭到世世代代奴性的贬损,害怕自由……大家被奴颜婢膝和虚伪折磨得太惨了。”而恐惧和害怕的结果就是使大家想方设法地想要保护自己,把自己装在他们自觉得安全的“套子”里。像别里科夫那样循规蹈矩、墨守成规,挖空心思地“千万不要闹出什么乱子来”。就像兽医伊万·伊万内奇说的:“问题就在这儿。大家住在空气污浊、极其拥挤的城里,写些非必须的公文,总是玩儿纸牌,这岂不也是一种套子?至于大家在懒汉、无端找麻烦的家伙和愚蠢而闲散的女性中间消磨大家的一生,自己说也听人家说各种各样的废话,这岂不也是一种套子?”的确,挖空心思地与大部分人维持一致,尽可能不出头露面,过着与大部分人同样的生活,这确实可以使人相安无事地终其一生,但却残害了多少心灵,甚至抹杀了几天才啊!如此的生活如何会不叫人烦闷呢?长此以往,如此的生活培养了人的惰性、懒散和无聊。作为深刻洞察俄罗斯人心理特质和民族劣根性的伟大作家,契诃夫除去倾力表现俄国人的奴性及其产生的根源,他还倾注了很多的笔墨表现俄国人的无聊和烦闷。这是他创作中的又一个尤为重要的主题。
“不可以,再也不可以照如此生活下去了。”这句发自肺腑的话应该是契诃夫写这篇小说的最后目的,是这部小说的最强音,也是他写作相同种类小说的宗旨。假如说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大师,如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塑造了一系列“小人物”的形象,对他们寄托了深切的同情和怜悯,那样,到了契诃夫这里情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大家举出的几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都算是“小人物”,但作家笔端流露出的指责却远远多于同情,是批判,批判他们本身的软弱无能,指责他们不知自尊,在有权有势者面前卑躬屈膝。所以说契诃夫表现的不是“小人物”,而是妨碍他们成为真的的人的东西,由于在契诃夫的心目中人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小人物”,他觉得一个人“应该意识到我们的尊严”,一个诚实的人“不可能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一个人不可以由于自己地位的卑微而贬低我们的尊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大写的人。在给友人的信中契诃夫写道:“应该写如此一部小说,表现一个青年,一个农奴的儿子,一个以前的小商贩,一个受过官职尊卑教育、吻着神父的手、膜拜其他人思想长大的初中生和大学生是怎么样一点一滴地摆脱掉自己的奴隶印记,表现他怎么样在一个明媚的早晨醒来,发现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的已经不是奴隶的血,而是真的的人的血。”
契诃夫的戏剧《万尼亚舅舅》中的大夫阿斯特洛夫说过的话代表了作家本人的追求和理想,他说:“人身上的所有都要是美好的:面孔,衣服,心灵和思想都要是美好的。”假如说契诃夫塑造的奴性十足的人物形象更生动,更具说服力,假如说契诃夫最后也没塑造出那样一个“在明媚的早晨醒来将来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自由人”的人物形象,那只能说明年代决定了这一点。契诃夫生活的年代是俄罗斯近代史上最为动荡、精神与经济危机最为紧急的年代,是一个没英雄的年代,俄罗斯的农奴规范虽然在契诃夫降生的第二年就废除去,但数百年的农奴规范却在俄罗斯人民的民族特质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根除的。作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最后一位古典大师,契诃夫与他的前女友们面临的是一些不一样的人物,生活的场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他更多关注的是当时历史舞台上的普通人与普通人身上的弱点。当把普通人的这种种弱点放在俄罗斯民族历史的大背景上来考察的时候,他的作品就带有了更高度的概括性。他把这种种的弱点甚至丑陋展示给读者,是为了让读者警醒:你一个人身上是不是有这类弱点,你一个人是否如此一个缩手缩脚、什么都怕的“套中人”,你离美好的理想有多远。
与前人相比,契诃夫不只在表现内容上有所不同,而且如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所言,他“创造了全新的书写形式”。这第一体目前他改变了文学形象的塑造办法本身,他的小说以表现各种各样的人物为主,但他却舍弃了传统的、细腻的肖像描写,在他那里最详细的肖像描写也没超越十几行的,因此他的作品总的风格是短小精悍、言简意赅。代替肖像描写的是比喻,是对服装的典型细节的表现,如“套中人”别里科夫:在这里作家详细地描写了主人公的物件,像套鞋、伞、眼镜、帽子、各种小套子和房间的摆设,却惟独没面部描写。但在几乎没涉及外貌的状况下契诃夫却细致而准确地展示了别里科夫的心理状况,即恐惧。别里科夫是一个尖酸刻薄、神经衰弱、精神极度紧张警觉的人的形象。关于省略肖像描写或极少肖像描写,契诃夫本人说过如此的话:“描摹一般的外貌恐怕画蛇添足;彼得堡不是西班牙……”言外之意是说:在阳光灿烂的西班牙海滨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和爱情的喜悦或者忧伤,那里的人面孔上的表情和形体动作是丰富多变的,值得一写的。可是在彼得堡,在像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中那样的外省小城市里,受恐惧控制的大家想方设法地磨去我们的棱角,力求与其他人维持一致,那样万人一面的外表又有哪些必要去浪费笔墨呢?就像契诃夫研究专家剖析的那样,契诃夫忽视肖像描写是由于他想要表现的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而是“一类人”,他真的的表现对象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一群人”,不是个体,而是群体。
因此,契诃夫的创作虽然是以俄国生活为背景,以夸张和讽刺的笔触表现的是俄国人的劣根性,但细细读来,他的作品对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人都具备深远的意义:他鼓励大家在任何状况下都不可以舍弃我们的尊严,要消灭精神奴役,追求平等、自由、勇敢和心灵的纯洁。列夫·托尔斯泰说过,契诃夫是“一个生活的艺术家……他创作的价值在于,他的创作不只让任何一个俄国人了解,感到贴切,而且让每个人了解并且感到贴切。这是主要的。”而这也就是契诃夫创作的真的意义和永恒价值。
1f6a